|
|
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注册

×
作者:微信文章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集刊
AMI(2022)法学入库集刊
*本文刊载于《“一带一路”法律研究》(第9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3-19页。

作者简介
黄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海事及海商审判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研究方向:国际私法、民商法。
万浩,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自由贸易区法庭(自由贸易区知识产权法庭)法官助理,研究方向:民商法。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纵深推进,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交往日益加深。中国与有关国家的进出口数据在2013—2022年期间,实现了年均增长量8.6%,2022年度有关进出口贸易数据仍在快速上升,共计13.83万亿元进出口,比上一个年度增长19.4个百分点,其中出口为7.89万亿元,进口为5.94万亿元。繁荣经济贸易的背后,亦需要充分的司法保障,《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便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国际货物贸易的关键法律依据之一。目前,中国已与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达成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有关文本。同时,《公约》的缔约国数量已达到96个,几乎涵盖了除英国以外世界主要经济体,有关缔约国之间的国际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总额的2/3。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与《公约》所涉缔约国高度重合,如俄罗斯、法国、德国、白俄罗斯、蒙古、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立陶宛、老挝、越南、柬埔寨、新加坡、丹麦、捷克、埃及、波兰、荷兰、塞尔维亚、伊拉克、意大利等均加入了《公约》。
在此背景下,如何用好《公约》维护“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与中国贸易的稳定性,充分发挥市场活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实现贸易健康发展,是中国司法“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主题之一。而《公约》第7条第2款所规定的一般原则优先于国际私法规定适用之法律,[1]作为《公约》兜底性规定,在适用上具有较大的法院裁量空间。若判定不准,极易导致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失衡,有违《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所要求的“共商、共建、共享”之原则。本文即以上海法院审结的一起“德国坚恩公司与上海纺织装饰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为研究对象,探讨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正确处理《公约》的一般原则适用问题。
一、德国坚恩公司与上海纺织装饰公司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案情
(一)基本案情
2020年4月17日,德国坚恩公司作为买方,与卖方上海纺织装饰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纺饰公司”)签署了标的为300万个非医用性防护口罩的《售货确认书》,合同对价为三百六十余美元,运输方式为FOB上海。
德国坚恩公司于合同签订当日就付款362.2万美元给上海纺饰公司。后因上海纺饰公司委托的口罩生产商万康公司出现问题,相关口罩没能按约交付。2020年4月,有关口罩生产商直接向德国坚恩公司关联方退款500万元人民币。同年6月,上海纺饰公司再次退还93万美元给德国坚恩公司;同年8月5日、8月12日、8月19日、8月26日、9月1日、9月8日、9月17日,上海纺饰公司分别每次向德国坚恩公司退款10万美元;2021年3月9日、3月25日、4月7日,上海纺饰公司分别每次向德国坚恩公司退款5万美元。
2020年7月28日,上海纺饰公司员工华某某出具了一份《还款计划》,向德国坚恩公司表示:①第一批500万元人民币(约70万美元),从2020年8月4日起的每周二/三,每次还款10万美元;②第二批500万元人民币(约70万美元),从2020年11月10日起的每周二/三,每次还款10万美元;③第三批余款约400万人民币(约58万美元),于2020年底前再具体协商。《还款计划》落款为“上海纺织装饰华某某”。
2021年12月27日,上海纺饰公司发送了一份《联络函》给第三人杨某、周某,其内容为,第三人杨某、周某才是案涉的口罩出口业务的实际控制者,上海纺饰公司只是代理商。口罩生产商也都是第三人杨某、周某安排的。上海纺饰公司签署合同以及签署后续的口罩采购合同,都是根据第三人杨某、周某的安排。2020年4月17日,上海纺饰公司收到德国坚恩公司支付的合同款364.2万美元[2] ,同日上海纺饰公司根据第三人指示向万康公司支付口罩款人民币2281.59万元。后因万康公司无法依约交付货物,德国坚恩公司要求返还已经支付的货款。经第三人与万康公司、德国坚恩公司交涉解约及退款事宜,上海纺饰公司于2020年4~5月期间收到万康公司的退款人民币365万元,并于2020年6月~2021年4月期间陆续向德国坚恩公司退还货款178万美元,其中上海纺饰公司垫付资金共计人民币6 379 355.75元。
后因上海纺饰公司未能在期限内退还德国坚恩公司剩余货款1 156 811.22美元,故德国坚恩公司诉至法院。
德国坚恩公司诉称:德国坚恩公司(作为买方)与上海纺饰公司(作为卖方)签订了标的为300万个非医用性防护口罩的《售货确认书》,但上海纺饰公司未能在期限内归还德国坚恩公司剩余货款1 156 811.22美元,故要求法院判决上海纺饰公司退回货款,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上海纺饰公司答辩道:上海纺饰公司在本案中与第三人周某、杨某存在间接代理法律关系,所以,和德国坚恩公司签订《售货确认书》的行为是代表委托人所为;而且在签订合同之前,德国坚恩公司就明确知道上海纺饰公司与第三人的代理法律关系,所以《售货确认书》的合同当事人实为德国坚恩公司和第三人,故上海纺饰公司不同意德国坚恩公司诉请,要求驳回起诉。
第三人杨某、周某述称:上海纺饰公司和他们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二)裁判结果与理由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最终于2022年8月29日作出(2021)沪0115民初103940号民事判决,判决:“原、被告之间案涉的《售货确认书》于2020年4月22日被宣告无效;被告上海纺饰公司应当退还原告德国坚恩公司剩余的110余万美元的货款,并赔偿由此导致的有关利息的损失。”原、被告双方在法院作出判决后都没有提起上诉,该案判决也已经成为生效判决。
关于《公约》的适用,法院认为:“本案系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因原、被告的营业地所在国均为《公约》的缔约国,并且案件当事人也没有作出排除《公约》适用的一致性意思表示,故本案应自动适用《公约》。《公约》明确规定了关于未明确解决的属于《公约》范围的问题,所依据的一般原则具有优先性,只有不存在可适用的一般原则时,才可基于最密切联系原则寻求法律处理。”
关于《公约》一般原则的释明,法院认为:“虽然《公约》未有确切之规定,但合同相对性之原则在所有《公约》约束的合同中均可以适用,属于《公约》之一般原则,而作为一般举证责任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也同样属于《公约》之中有相应法律约束力的一般原则范畴。”
关于如何具体适用一般原则,法院分析到:“本案所涉及的合同就是双方签订的《售货确认书》,该确认书在当事人之间形成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并且原告业已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合同已处于履行阶段。被告主张其和第三人之间存在代理关系,合同当事人为第三人,而非被告。但综合案情观之,被告的抗辩不能成立。从法院认定的合同订立过程看,《售货确认书》与《采购合同(口罩)》相互印证,证明案涉合同及其后续采购事宜的存在,而案涉合同之中并未存在第三人。即使是从合同签订和磋商所涉及的微信聊天记录看,第三人都是代表着被告的工作人员,进行合同签订,且最终合同内容的确定也需要被告方进行后续认可,从当事人法庭陈述看,第三人也始终认为其代表着被告进行相关合同磋商行为。因此合同系在原、被告之间成立具有相应的事实予以佐证。而被告主张的代理关系并未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事实存在。此外,在退款的过程中,也是被告进行了相应的退款行为,且系被告向原告的有关公司退还。而《还款计划》对于如何还款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落款处也是以被告公司员工的名义签订的。即使被告自己否定了证据的真实性,但《还款计划》和事实上的部分退款都是相互呼应的。因此,法院认定的合同相对人是原、被告。”
综上,法院认为,被告因未能按时交付货物构成了违约,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相应的退款行为,构成了《公约》所述的宣告合同无效之行为。基于《公约》第81条之内容,宣告合同无效使得当事人权利义务被解除,但损害赔偿责任依旧存续。原告有权要求被告退还相关货款。此外基于第84条第1款之内容,支付价款利息也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故本案中,法院依法支持了原告关于退还剩余货款以及相关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1]
二、“一带一路”场景下《公约》的
适用要求
本文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讨论《公约》的一般原则的适用问题,是聚焦于中国法院受理的涉及“一带一路”国家的涉外商事纠纷的法律适用。在讨论该问题时,首先需要明确何种情形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商事主体发生的纠纷可以适用《公约》。例如本案当事人营业地均为《公约》缔约国,符合《公约》第1条第1款第a项的适用规定。但是当事人在合同中并未明确表示对《公约》之适用,此时《公约》能否适用呢?
(一)《公约》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适用规则
1.《公约》与“一带一路”协议规则的关系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发起的倡议项目,系一项系统工程,并未外化为区域性国际组织,其本质上是一个跨国、跨地区开展的国际合作项目,本身并不属于条约框架。但是,基于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日益增多,中国在“一带一路”项下和很多国家达成了双边协议。截至2023年6月,中国已经同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1]这些双边或多边协议中多强调“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核心要旨,继而在经济、能源、安全等多领域深化彼此合作。
在此基础上,《公约》和这些“一带一路”项下协议是否存在适用上的冲突呢?其一,《公约》明确了“其他国际协定效力优先原则”。[2]《公约》第90条规定,本公约不优于业已缔结或可能[2] 缔结并载有与属于本公约范围内事项有关的条款的任何国际协定,但以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均在这种协定的缔约国内为限。这意味着在同等情况下,《公约》的规定与其他国际协定有冲突时,其他国际协定将优先适用。一般认为,这里的国际协定既包括多边条约,也包括区域性条约、双边条约,不仅包括现有的国际条约,还包括未来有可能签订的国际条约。《公约》如此规定,主要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在《公约》与“一带一路”项下协议的关系上,在同等条件下“一带一路”项下协议优先适用。其二,“一带一路”项下相关协议在协议内容上,与《公约》的规定一般不存在冲突,且多为框架性、原则性的规定,其协议精神也和《公约》的立法精神相吻合。在适用《公约》的同时,亦是对于“一带一路”相关协议义务的履行。在适用《公约》进行各国商主体纠纷解决时,当然也是对于各国所应负有的“条约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的尊重,从这个视角出发,适用《公约》完全符合“一带一路”相关协议“互尊互信”的核心要旨。同时,从《公约》本身的效力规定看,其旨在形成统一调整国际商事争议的规则体系,在符合《公约》第1~5条规定的调整范围时,若“一带一路”相关协议没有规定或没有不同规定,《公约》优先于冲突法及相应的国内实体法而统一调整国际商事争议,这是对《公约》规定进行法律解释的当然结论,反映出《公约》的统一性、自治性、国际性。从这种意义上讲,《公约》一般会被优先适用。
2.《公约》在共建“一带一路”缔约国的优先适用
《公约》想要在个案中运用,就需要要求相关国家系《公约》的缔约国。就中国而言,原《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在现行《民法典》框架下,该款已删除,是否意味着民商事条约在中国不再直接适用,须经国内法之转化?
本文观点是,仍可直接适用。其一,《民法典》虽然未能沿袭原《民法通则》第142条关于国际条约的适用规定,但2021年《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第19条明确《公约》自动适用的效力。[3]2023年颁布的《对外关系法》第30条亦明确了国家“善意履行有关条约和协定规定的义务”[3] 。最高法院“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诉蒂森克虏伯冶金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指导案例亦肯定了这一观点。[4]从国内司法视角看,直接适用《公约》并无不可。其二,从《公约》的本身规定看,第一章适用范围均从具体的合同法律关系特征出发,确定此公约能否适用。从《公约》的缔约意旨看,其本身即欲达到自动适用国际销售合同纠纷之法律效果,从而满足在国内法的体系外建立起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统一规则的立法目的。中国作为缔约国,显然需要履行“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义务。[5]而其他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若是《公约》的缔约国,则同理得适用《公约》。
(二)纠纷当事人的营业地需为《公约》缔约国
中国受理的涉“一带一路”商事纠纷,若想适用《公约》,首先需要满足《公约》第1条第1款第a项之规定。因为中国对于《公约》第1条第1款第b项作出了保留,故而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当事人营业地均为《公约》缔约国,此外案涉合同关系是《公约》调整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一带一路”场景下界定合同当事人的营业地所在国是否为《公约》缔约国,是在中国适用该公约的前提。
在涉“一带一路”商事纠纷中,一种情形为,合同当事人的营业地为中国和“一带一路”共建的他国;一种情形为,合同当事人的营业地均为“一带一路”共建的他国,当事人基于其他连接点诉至中国法院。上述情形中均需判断他国是否缔结了《公约》,若确为缔约国,则符合《公约》规定的适用范围。
(三)《公约》若无当事人明确合意排除即可适用
在符合《公约》规定之上述适用范围时,若当事人没有明确排除《公约》适用,则《公约》就应当适用。一则,从《公约》的体系解释出发,其第一章共计6条,对适用范围进行详尽规定。其中第6条是对前5条适用范围之补充,基于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规定当事人“可以不适用本公约”,从其行文逻辑看,前5条已经从客观方面明确了《公约》在何种情形下得以适用,第6条则是当事人主观能动地排除《公约》适用,其言下之意原则上是应当适用的,只有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的方式予以排除,方能不适用本公约。二则,从立法目的角度出发,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也明确表示,基于第6条,各国法院需要“提高不排除本公约适用性的要求”,[6]即要求各国在适用本公约时,以适用为原则,不适用为例外。三则,2021年《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第19条亦表述为“但当事人明确约定排除适用该公约的除外”[4] ,其除外情形亦和本案的观点一致。故而如本案之情形,可以适用《公约》。
三、《公约》内未决事应首先
通过具体的《公约》一般原则解决
(一)《公约》内未决事宜应当首先考虑《公约》一般原则
在本案中,被告所主张的代理关系,《公约》本身并没有条款予以明确,属于未决事宜。考量被告所述的抗辩内容,其主张表观上看,合同书面所载的签署方确实是原、被告,但是被告是基于其和第三人代理的原因关系,致使其签署相应合同。故而被告仅为居中的代理人,在原告签订《售货确认书》时也是知晓第三人是合同的实际当事人,故而第三人才是合同当事人,因此本案的相关义务也应当是由第三人负担。被告所谓的主张,是认为其和第三人之间的是间接代理法律关系,因为第三人是案涉合同的委托方,所以合同当事人是第三人。故,此时首先需要明确,适用《公约》还是基于国际私法规则找寻对应的准据法。
依据《公约》第7条第2款,对《公约》内的未决事宜,《公约》依据的一般原则具有优先性。根据上述规定,《公约》内的未决事宜优先是通过《公约》依据的一般原则来进行分析。故而,若不讨论是否存在可适用的一般原则,就直接在中国民法框架下分析间接代理关系是否存在,就可能导致法律适用方面的瑕疵。
此处,需要进一步厘清与《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第18条的关系。该纪要第18条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对涉外民商事案件中的具体争议没有规定,或者案件的具体争议涉及保留事项的,人民法院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法律的规定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1] 该条是指国际条约没有规定或者涉缔约国保留事项,适用冲突法确定的准据法。然《公约》第7条第2款并非属于该种情形,该款明确规定了属于《公约》范围内但《公约》未明确事项依照一般原则来处理,不属于上述纪要第18条所述条约没有规定的情形。如果《公约》没有详细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确定准据法以审理案件。而是应当明确条款所依据的一般原则,通过一般原则在《公约》的范畴内分析案情,只有在《公约》中的一般原则也无法处理相应法律问题时,再行通过国际私法规则确定案件适用的准据法。
(二)一般原则应当基于《公约》内容与国际商事惯例予以合理明确
从理论出发,若运用原则处理问题,其具有前置性条件,也就是在穷尽规则之后,方能运用原则处理具体案件。[1]那在公约框架下,一般原则如何确定呢?此时,必须充分论证该一般原则确为公约所依据之原则,相应的一般原则才能够运用到个案中,不能随意运用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概言之,公约内容和国际商事惯例可以协助确定相应之原则。
以合同相对性原则在上述案件中的适用为例。合同相对性,一般系指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从国际私法角度观之,其内涵主要为,合同约定之权利义务内容通常只能约束合同当事人,而不能突破当事人来约束他人。本案为何认为合同相对性原则系《公约》的一般原则呢?首先,从体系解释的路径看,《公约》相关措辞均为“买方、卖方、特定的人、双方当事人”,其中提及第三人的条约条款规定的内容也是直接约束第三人,即“必须是第三方不能提出任何权利或要求的货物”。[3]在合同订立过程中的“发价与接受”的法律框架下,也不曾涉及对第三人法律行为之约束性规定。综合来看《公约》的内容设计,《公约》调整的是典型的买卖合同,对于涉及第三人的合同并无规定,亦无约束合同外第三人的立法意图。其次,从国际法比较视角看,合同相对性原则是罗马法悠久的原则之一,也是国际贸易中广泛认可的商业管理,从而确保合同当事人可以预期参与者,提升交易的可预见性和安全性。最后,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在2016年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判例法摘要汇编》(以下简称《公约判例法摘要》)中亦列明多国在适用《公约》时运用了合同相当性原则。[4]综上所述,合同相对性原则为《公约》的一般原则之一。
此外,根据《公约判例法摘要》的内容,《公约》中的一般原则可能还包括:意思自治原则(第6条)、诚信原则与禁止反言原则(第7条)、合同形式自由原则(第11条)、减少损失原则(第77条)、遵从国际贸易惯例原则(第9条)、宣告合同无效作为最后救济手段原则(第49条和第64条)、充分赔偿原则(第74条)、债权人延迟支付时要求支付利息原则(第78条)等。[5]对上述规定涉及的一般原则,在具体运用时应予以高度重视。
(三)一般原则可考虑“一带一路”各国间的商事交易习惯
“一带一路”背景下着眼于《公约》条款的文义解释和国际商事惯例之外,还需注意对共建“一带一路”各国间业已形成的商事交易习惯的尊重。所谓各国间的商事交易习惯,就是各国在彼此进行国际商事交往时,形成的相关习惯。
事实上,基于各国的国情差异、风土人情差异,其各自在国际商事交易中遵循的商事交易习惯也各有不同。例如在处理欠款利息时,保加利亚工商会仲裁法院就认为,一般原则要求向债务人发送正式通知后才能支付欠款利息。[6]而斯洛伐克加兰塔地区法院、克罗地亚高等商事法院、塞尔维亚那斯拉夫商会附属外贸仲裁院、俄罗斯联邦工商会国际商事仲裁院则认为,利率问题根本不受《公约》管辖,根据《公约》第7条第2款的规定,利率的确定留待通过诉讼地国际私法规则所确定的适用法律来解决。[7]当中国法院处理不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纠纷案件时,需要注重相关国家企业对于其国际商事交易习惯的论述,并进而判断其是否可以作为《公约》第7条第2款的一般原则,运用到案件的实际审理中。
从理论上说,各国间的商事交易习惯因为未能在一般国际商事交易主体中形成共识,亦未被各国所承认,只能构成区域性的交易习惯。在此基础上,中国为何还要在《公约》的一般原则中,考量“一带一路”各国的商事交易习惯呢?
第一,从中国的“一带一路”框架出发,其应当尊重各国的商事交易习惯。其重要的规范依据即为《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该规范性文件作为“一带一路”建设这一系统工程的详细阐述,是中国对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重要承诺。其中“二、共建原则”规定:“……坚持和谐包容。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坚持市场运作。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在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中,中国应当恪守共建原则中“和谐包容、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的相关内涵,不应机械地仅从国际通行惯例的角度阐释一般原则,要充分尊重相关国家在国际商事交易中形成的相关习惯。
第二,从“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双边或多边协议出发,考虑各国间的商事交易习惯是中国应当履行的协议义务。前文已对“一带一路”基础上,中国和各国订立的相关协议进行了介绍,中国应当履行协议中与各国之间就经济领域的“互尊互信”的相关承诺。而《公约》的一般原则适用,本身具有较大的司法裁量空间,中国存在履行“一带一路”相关协议义务的条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形成的交易习惯,虽然尚未达到国际惯例的通行程度,但是作为区域性的交易习惯,在涉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国际商事纠纷中,予以适当考量,显然是“一带一路”项下协议所应有之义,也可对共建“一带一路”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当然,对于“一带一路”各国的商事交易习惯的尊重并不意味着对相关交易习惯的绝对接受。法院需要结合实际案情考量,在充分说理后,作出是否将其纳入一般原则的司法判断。
四、一般原则适用路径需
借助合同释义与举证责任分配
(一)基于《公约》对合同内容进行客观主义解释是原则运用前提
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是适用原则的基础所在。而在国际销售合同纠纷中,合同内容如何释义,从而确定当事人意思表示为何,便是案情分析的重要环节,故也是适用一般原则的重要前提。
上述案件中,法院也是通过对合同条款的文义解释确定了原则的适用。因为《售货确认书》的签订主体就是原、被告,所以原告要求被告作为合同主体履行义务。被告则主张其签署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其作为第三人的代理人,代第三人签署该合同,其本身不是合同缔约方,相关的合同义务在第三人身上。此时,解释被告签署合同之意思表示究竟为何,是案件的关键所在。根据《公约》第8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的意思表示需要结合其意旨进行解释,而解释的前提是合同相对人需要知晓或者应当知晓当事人的相关意旨。从《公约》上述内容的要求看,《公约》对意思表示之解释也是需要从客观主义进行思考,而不能单纯从当事人主观角度进行考量。关于如何解释,《公约》第8条第2款亦明确规定:“应按照一个与另一方当事人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应有的理解来解释。”[1] 在解释被告签署合同的行为究竟是其作为合同当事人还是第三人代理人身份,就要从一般理性人视角,可观看其订立合同的相关事实应当被理解为当事人还是第三人代理人。
此时结合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有关理论,涉案合同签署处系被告名称,表观应当推定其为当事人,而第三人作为无法表观推之的合同外人员,只有满足特别条件,才会受到合同约束,具体至本案,也就是相关代理关系确实存在且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存在代理关系,被告的行为约束的是第三人,此时合同才能够约束第三人。[1]
(二)当事人举证责任分配是适用一般原则的重要路径
上述案件中确定合同相对性原则适用之后,由谁来负有举证责任以证明是否存在突破合同相对性之情形?这是一般原则运用的重要问题之一。只有明确了原、被告就合同相对性各自的举证责任为何,才能准确地适用合同相对性原则。举证责任的分配是一个程序法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70条明确规定涉外民事诉讼程序涉外编的优先适用以及其他编的补充适用,在涉外民事案件的审理中还是以本国有关的程序法进行审理,基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基本证明责任规则得以运用。[2]
然而,国际条约的优先适用亦为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之内容。[3]《公约》如果有不同于国内程序法的举证责任分配,就存在适用《公约》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空间。正因如此,法院在上述案例中也对“谁主张,谁举证”属于《公约》的一般原则进行了相关的论述。其一,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公约》的条款是具有“谁主张,谁举证”这一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意旨,例如《公约》第79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不履行义务,不负责任,如果他能证明此种不履行义务,是由于某种非他所能控制的障碍,而且对于这种障碍,没有理由预期他在订立合同时能考虑到或能避免或克服它或它的后果”[4] 时,得以免责。这一条款将障碍情形发生的举证责任划分给了因为这种障碍导致无法履行合同义务的当事人,也即主张的一方。该条款的内涵恰恰反映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其二,“谁主张,谁举证”是历史悠久、实践丰富的法律原则。早在罗马法时期就形成了相关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的法律规则[4],自然应当适用。其三,《公约判例法摘要》也有将“谁主张,谁举证”作为一般原则的案例。[5]上述案例即运用了“谁主张,谁举证”这一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从而对合同相对性原则加以运用,即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主张间接代理的被告,进而最终定分止争。
结语
《公约》系国际货物销售领域内的重要国际法源,历经四十余年而越发显示出生命力,几乎涵盖了除英国以外世界主要经济体,其缔约国间的国际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2/3,被誉为“最成功的实体统一商业法条约”。同时,《公约》规则直接影响着我国合同法的相关框架设计。因为两者间的差异不大,审判者极易直接运用国内法规则审理案件,从而使得法律适用存在瑕疵。而《公约》“一般原则”是兜底性条款,法院在解释一般原则时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本文着眼于《公约》一般原则的适用规则,借助《公约》条款的体系性解释以及国际商事惯例的运用,适用具体的一般原则。中国需要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共商、共建、共享”之原则,对于具体涉案缔约国业已形成的国际商事交易习惯予以考量,在充分尊重各国间商事习惯差异的基础上,考量其与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的一致性,从而做到求同存异、兼容并蓄,最大限度发挥《公约》一般原则在构建“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有益效果。
Application of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CISG)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Commentary on the Dispute Case over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between German Company Janken
and Shanghai Textile Company
Abstract: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CISG) serves as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legal source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by accurately using the convention to regulate business behavior, is one of the ways to promote the initial wish of the “Belt and Road”. Article 7 of the Convention provides that matters not expressly settled in the Convention but falling within its scope shall be resolv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n which the Convention is based. In the absence of such general principles, the applicable law shall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However, the Convention does not explicitly explain what these general principles are nor does it provide for their application. In practice,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it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principles of consultation,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while respecting the relevant business practices already formed by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y combining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ustoms and legislative purposes, specific general principles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and strictly appli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onvention, thereby promoting uniform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and ensuring its coherence with rule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ISG; General Principles


往期推荐
《“一带一路”法律研究(第9卷)》目录

《“一带一路”法律研究(第10卷)》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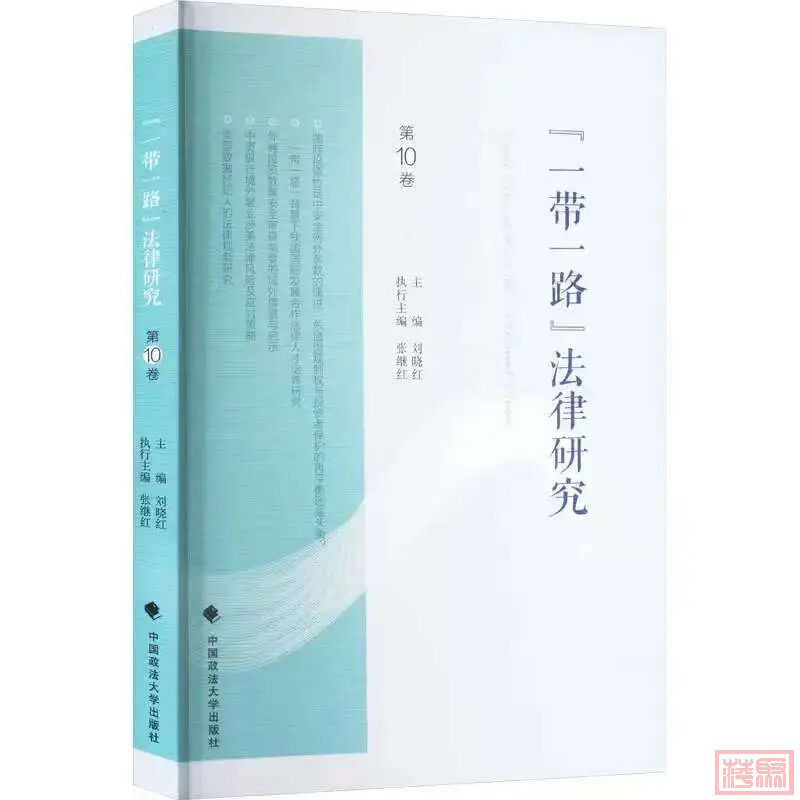
《“一带一路”法律研究》征稿启事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
即可购买《“一带一路” 法律研究(第9卷)》
主办单位:
《“一带一路”法律研究》编辑部



原创合作及交流合作请联系:56855931@qq.com
编辑、审核:张继红
阅读原文 |
|